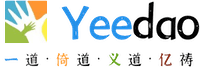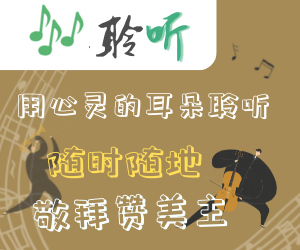按:富不过三代,信,有时也传不过三代
来甬城放空两天,好山好水好人,实在惬意。不过休闲之余,免不了谈起当地的情况。
聊到一间40多年历史的会点,信众不少、自由教产,听起来形式一片大好。
然而,常见的问题无非就是老年化严重和老中青三代断层。非一线城市里似乎普遍存在此等问题。当然,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新兴er之中,大多数可能都还没到三代传承,暂时显不出来这个问题。
而且,似乎模仿某些密宗传男不传女一样,信不过三代的问题在男性后裔之中看起来更加普遍。
这背后当然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,不过我们改变不了世代,也许可以从这一代的我们的改起。
第一代人开疆破土、实在辛苦;第二代人只管将家业守住、舒舒服服,第三代人出生就自带祝福、但不少也信的稀里糊涂。
从第一代“亚伯拉罕们”的角度来说,信仰两条腿——话语和祈祷,再以信靠和顺服回应。如此便完全了那一代人的义,忠心到底不要变节即可。他们行善没有丧志,到了时候就结出果子来了。
然而到了第二代“以撒er”,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。以撒的信仰看起来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,只要老老实实继承就好了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些处境化的突破就不错了,至少他开始了挖呀挖呀挖的井旁敬拜。当然,他也如父一样,撒了个“小谎”。断层超过继承,创新也不是没有,但实在不多。
第三代的信仰状况呈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,“雅各们”有树乘凉,住在井旁。喝着祖辈们打下的水,却忘记了谁给他们挖下的井。过去发生的一切好像就真的只是一个个家庭故事、文化叙事,不再具有鲜活的意义,也难以与祖辈并他们所拜的产生认同感,更不要提给他们支持回应当代的挑战了。
所以,雅各最后逃离信仰之家也并不奇怪,就像第三代人往往都要经历这么一段离开与归回的路径一样,只不过,希望不要一晃二十多年,人到中年才知回转。
这个模式其实一直在出现:
第一代摩西、约书亚打下迦南天下,那神迹奇事伴随着应许,天天经历得如同云柱火柱般明显的带领,还有拿着刀的元帅在前头引导,那个信仰是鲜活的,是令人振奋的。“至于我和我家,必定侍奉耶和华”是激励这代人的异象。
第二代得地的以色列人大概不需要异象,因为抓得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:不再居住帐篷,有房产、有土产,无需再去打仗。只要守住已有的地方、再赶走剩下为数不多的迦南人即可。但,很明显,那史诗般的民族历史渐渐成了过去,与上一代人的隔阂逐步加深。
第三代人渐渐变得跟迦南人无异。这代人要么是孕育了“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,个人任意而行”的一代人,要么自己就是其中一员。敌人被踩在脚下的故事看起来毫无可能、那些真实的应许似乎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从听神的话,到听神话,不过是二三代人的事。他们也不想管其中的差别,还是生存要紧,哪怕活得憋屈一点也行。
连大卫家也难逃此循环:
第一代大卫,逃亡、逃亡、再逃亡,好不容易等到应许落实在他的身上,早已不是那个翩翩少年。久经历练、捶打,他的确是主所预备的器皿,甘愿被使用作百姓的忠仆。
第二代所罗门,用大卫积累的财富建造了圣殿。当然,还有自己那豪华的宫殿。他应有尽有,却失去了他起初竭力祈求的智慧——从敬畏开始的智慧。他一生的前半段大抵跟随父辈,后半段随着自己,也为后代种下了灭亡的种子。
第三代罗波安真正演示了什么叫民无异象就放肆。好的一点没学会,连父亲的政治智慧也是一点没搞懂。身边的狐朋狗友反成了智囊团,迅速把家业败得只剩一星半点。在他身上不要说看到信徒的影子了,连个有常识的人都不如,纯纯败家子。
三代现象当然不只出现在教界,然而它不打折扣地、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在信仰传承中,倒是叫人遗憾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,不知道那逼迫人的是否也同样摸出了这个门道,放弃对第一代人的逼迫,转而集中精力围追堵截第二代人、第三代人。很明显,这是事半功倍的计谋。再加上我们的不重视、不作为,信不过三代的魔咒似乎很难打破。
上一辈人刻苦己心、为主受苦,当跑的路他们已经跑了,美好的仗也已打完。但除了感慨他们的忠心与受苦,也得面对一个同样普遍的情况,就是真的有家庭见证的是不太多的。
可以理解以当时的处境,服侍者因各种内外困境而疲于奔命,根本无力顾及自己的家庭。毁家服侍是不少的,这点叫人惋惜。但这如果成为了效法的模式而不顾现实,最后只能是一面拉人从前院进来,一面开着自己的孩子从后院溜走。
在浙江——这个深深被恩典浸泡的大省中,有不少信二代、三代只保留了遗传性的信仰:对信仰的认识跟民间宗教并无区别,至于那些核心的教义不要说经历了,连信可能都很困难。他们能说的,多半是父辈、祖辈那些神奇的经历,在自己身上却鲜有此等事迹。
外包装和上辈人一样,却完全不是那个配方。
“让我不信是不可能的,但是让我好好信也是不可能的”,某人如是说。第三代还没有败得太干净,至少保留了一些礼仪和文化,但那个核心早就不是那个道路、真理和生命了。
不过,读读列王纪,或许有安慰:最敬虔的王往往后代乖张邪僻,可即使是最败坏的王也能拥有敬畏之子。看来,打破循环的,还得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主。
每一代人都必须照着自己被赐予的、在自己的处境里做出回应,方式或有不同,内核却不能变质。
除了那可以打破魔咒的更高深的魔法,我们还可以期待祂所设立的常规方法:我想到的就是家庭教育和门徒训练。
训练那能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,或许可以更具体地说,训练那能忠心教导下一代的父母与师长,让他们也忠心地用真理影响生命。如此,或许能在神圣护理之下,将信仰传承下去,跨越三代的魔咒。
一念及此,想起麦客的异象——装备麦客、收割麦子,我更看见此时工作的意义。专心搭建事工倍增的基础,开始一生二,二帶四的循环。
首要的是,作为这一代的信者,我希望我的信仰给下一代的观感是真实落地、可以经历的。我想开放自己,邀请他们观看并参与我的成败得失、高峰低谷。是的,尽管失败有时、也得胜有时;纵然灰心有时、亦更新有时。
当我的孩子们看见信仰真实地触及父母的每一个层面,或许,不只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刻下印记,也在他们的人生故事里留下美好的一笔。